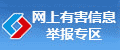长江商报消息 □严辉文
自由撰稿人,专栏作者。
村上春树是很有异性缘的。对此,他自己也毫不隐讳。村上在出版杂文集时,就连好朋友、画家安西水丸对他异性缘的评价也照录不误。有一段对话中,安西水丸调侃道:“所以他很讨女人喜欢啊。本来小说家就讨人喜欢,夫人平素只怕很不容易。哇,又说走嘴啦。”
或许,有人要说这要归功于村上小说的题材。村上善于写男女之事,男欢女爱,村上也不回避性描写。但这恐怕不是主要原因,写性话题,村上比许多作家更严肃、更收敛。有人说要归功于村上在小说中神出鬼没式的心灵魔术。何谓心灵魔术?笔者不揣浅陋,试着说上几句,心灵魔术就是始终行走在村上春树小说中又死死抓住读者的幽灵;是村上春树小说中的魔幻,又是村上小说中的写实;是村上小说中的现实世界,又是村上小说中的非现实;是村上细腻体贴引人入胜的对话,又是村上小说敲击心灵金不换的诗性语言。村上或许是最善于进行心理描写的小说家,村上确乎是用某种魔术掌控了读者。从这方面讲,村上或许契合了女性读者心灵方面的需要。
是的,村上春树曾经写过“足以让全国少男少女流干红泪”的“百分之百的恋爱小说”《挪威的森林》。是的,村上春树的几乎每一部小说,都或多或少离不开情色打底。是的,村上春树小说,时时刻刻满足了地球村时代、城市化时代、现代化时代都市女性的阅读需要。但是,就此将村上春树定位为“村上春色”,就大谬不然了。
小说离不开现实,真小说压根就回避不了批判现实、介入社会政治。村上小说,是否一味远离政治的小资情调,一味卿卿我我的“村上春色”呢?答案显然是否定的。事实上,无论是什么天才人物,只要刻意回避社会现实,他就写不了小说,至少写不了真小说。
与其说村上春树刻意讨好女读者,不如说,他作为优秀且有追求的小说家,必须刻意再现现实,连他所习惯于运用心灵魔术随意“穿越”的非现实世界,也是现实世界的倒影。即便是写恋爱故事、写都市小资的生存状态,村上春树也专注于揭示现代日本人的痛苦和沉沦、迷茫和孤独、彷徨和挣扎、失落与救赎。
我比较偏爱那本叫做《舞!舞!舞!》的小说。村上把作品背景设定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,而他所关照的视角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生存状态,所批判的正是“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”的种种不公。他运用诗性文字的灵巧鞭子,着力地鞭挞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那个“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”的体制之弊。这是一种文字与思想的巧妙组合,或许女读者们喜欢都也来不及呢。
那个“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”的体制本质就是“资本崇拜”、“资本至上”,“人们崇拜资本所具有的勃勃生机,崇拜其神话色彩,崇拜东京地价,崇拜保时捷那闪闪发光的标志”。在这种体制下,为了黄金地皮,大资本家铤而走险巧取豪夺,地方政府丢弃公平默许作恶。而在日本札幌市土地转让和旧城拆迁中,那个破旧的老海豚宾馆的落伍小老板面对土地剥夺,只有忍声吞气受尽凌辱——因为土地的背后除了资本,还有为虎作伥的地痞无赖、黑社会团伙以及权倾一方的政治家。破落的小老板,除了乖乖滚蛋就是“消失得像吸进了墙壁”一样。
曾经正直的记者和自由撰稿人,要么在不痛不痒的报道之后因受到威胁而保持沉默,要么学会适应那个“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”。开一个远离揭露行当的事务所,“对部下连哄带骗,使得他们俯首帖耳;在管财务的女孩面前开几句粗俗的玩笑,大把大把地利用经费把别人拉到银座夜总会”。
甚至于运用好可以随手报销的经费,也是那个体制的要求。即便那个看起来非常成功八面风光的电影演员五反田,也是如此。他可以运用经费住各种服务应有尽有的高档住宅,可以运用经费招徕高级应召女郎,可以运用经费享用玛莎拉蒂豪车,甚至于他苦闷无聊之际无意杀害了应召女郎,也必然是无法查清的无头案。但是只要他不按公司的意志行事,不演无聊无艺术水准的电影,拒绝与体制合作,甚至于妄想对抗那个体制,到头来,只有驾驶“玛莎拉蒂”坠海自杀一条路了。
责编:ZB